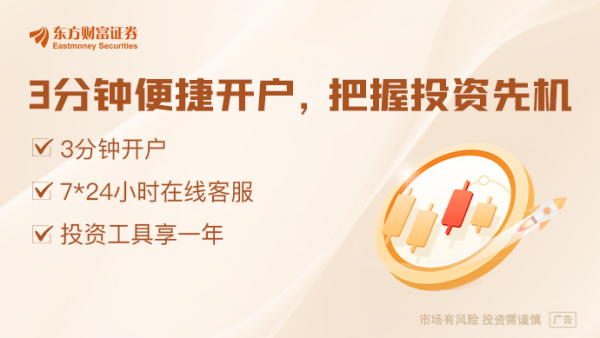大漠孤烟,残阳如血,一匹瘦马驮着少年自西而来。他衣衫褴褛,眉宇间却藏不住锋芒,像一柄未出鞘的剑线上炒股配资之家,静待惊雷。京城南城,老槐树下的石墩上,少年李昭放下行囊,目光掠过斑驳院墙与晾晒的粗布衣裳,落在那株年年开花的石榴树上。风过处,树影婆娑,仿佛在低语百年前那些金戈铁马、书生意气的旧梦。
第十三集,暴雨倾盆,胡同积水成河。李昭蹲在公用水龙头旁,为邻居王婶淘米,水花溅湿了裤脚。巷口传来京胡声,是瞎眼老艺人拉《夜深沉》。少年听着,忽然拾起地上的竹筷,在铁盆上敲出战鼓节奏。众人侧目,他朗声而笑:“此非悲曲,乃壮士出征之号!”那一夜,他用锅盖当盾,扫帚作枪,在积水的院中独舞长坂坡,惊得墙头野猫四散。石榴树下,几个孩童瞪大眼睛,仿佛看见传说中的少年将军重生。
第十七集,冬雪压檐,煤炉上炖着白菜豆腐。李昭与院中老教授对坐弈棋,黑白子落,如千军万马交锋。老人叹:“你锋芒太露,易折。”少年执黑子,轻敲棋盘: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。”话音未落,窗外传来拆迁队的脚步声。推土机的轰鸣碾碎晨梦,院中老墙刻着“仁义礼智信”的砖石簌簌剥落。李昭立于院中,手捧祖传砚台,墨汁倾入雪地,竟如血般蔓延。他不跪不求,只将一首《少年行》写在拆迁告示背面,字字如刀,刻入人心。
展开剩余51%第二十一集,夏夜闷热,蒲扇摇动如风。李昭在院中支起小桌,教孩子们写毛笔字。墨香混着槐花气息,飘过晾衣绳与竹竿。忽有电视台记者闯入,称要拍摄“京城最后的胡同少年”。李昭搁笔,淡淡道:“我不是标本,是活人。”他转身端出母亲腌的酱菜,分与众人,笑道:“尝尝这人间滋味,比镜头里的热闹真实得多。”那一晚,没有镁光灯,只有星空下朗朗书声,与远处地铁呼啸而过的节奏共鸣。
第二十六集,秋风起,石榴熟透落地。李昭收到边疆支教的调令。临行前夜,全院人聚在树下。王婶塞来一包腊肉,老教授赠他半部《史记》,瞎眼艺人吹起埙,声如裂帛。少年不言别,只将院中那口老井的水装入竹筒,说:“此水养我一年,胜过千言。”黎明时分,他背着行囊走出胡同,背影融入晨雾。身后,石榴树忽然落下一枚红果,砸在石阶上,迸裂如星火。
剧终时,镜头拉远。高楼林立间,那片胡同已成工地。可某所边陲小学的黑板上,写着“鲜衣怒马少年郎”七字,笔力遒劲,气贯长虹。窗外,黄沙漫天,一群孩子正用树枝在地上临摹——他们眼中,有不灭的光。
少年未必鲜衣,未必怒马,但心中有火,足可燎原。市井深处,一粥一饭皆为道场;寻常巷陌,一言一行俱是修行。那株石榴树或许终将消失,可它投下的影子,早已长进少年的骨血线上炒股配资之家,化作脊梁,撑起一片朗朗乾坤。
发布于:河北省兴盛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